“即便我肯,你就舍得吗?”
“即便我肯,你就舍得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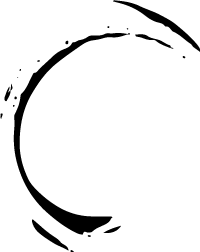
文/青语
一 破
夜黑得太蹊跷。
谁都睡不着,城南的火光冲天而起,焰色如霞,火树银花,一朵一朵在风里展放得奇丽,隐隐哭喊的声音,突如其来,又突如其止。
静谧里弦响,不成调,疏疏几个音,像是在弹给谁听。
巡视了大半个城,满目都见疮痍,半壁残垣,谁曾记姹紫嫣红?明知道是破城之后难免,但是风太凉,总还觉得萧索。
紧一紧风衣。
月亮出来了,纤细的影子,一半落在地上,一半折在墙边,疏密有致,浓淡相宜,如上好的水墨画,只缺了遒枝劲梅,婆娑如舞。
转一个弯,影子拉长,颜色自然淡去三分,瞬间尖啸而来的风,慕莘在凛冽的刀光中看见自己苍白的眉目,衣袂惊起,只来得及微微侧身,剑尚在鞘中,料想受伤不可避免,但随即一蓬热血,全泼在了脚边。
刺客倒在地上,眼睛还睁着,没有闭上,也闭不上了。
回眸看见重熙——自然是他,不用看也知道,只不知是几时到的,铠甲也没有穿,一身白衣,宽大的袖被风吹得猎猎,他反握住剑柄,在衣上胡乱擦几下,斑驳的血痕,很快就凝固了。
慕莘看了他一会儿,问:“怎么没去喝酒庆功?”

军中诸将这时候不是在城南杀人放火,就是聚在营帐里喝酒,猜拳,吹牛,赌钱为乐,难得一场大胜仗,几个月辛苦有了结果,这时候不乐,更待何时?慕莘是放心不下城中守卫,才轻身前来查看,重熙却是个爱热闹的。
“那些王八羔子够狠!”重熙拍拍空空如也的钱袋,露一个愁眉苦脸的笑容:“……输光了,只好出来躲躲。”
明明是担心她的安危,偏每次都能编出稀奇古怪的理由,就没一个正经的,慕莘忍住笑:“既如此,劳烦将军为我护驾。”
“能为慕帅鞍前马后,是我的荣幸。”重熙眉开眼笑,一口应承。
他长了不算难看的一张面孔,当然也说不上俊俏,分开来眉眼都寻常,凑到一起倒有些英气,只是平日嬉皮笑脸惯了,五官没多少机会摆在正确的位置上,这时候转身开路,侧容浸在月色里,倒有几分年少翩翩的意思。
慕莘略低一低头,影子叠着影子,空寂长街,一步步声如钟鼓,重合的音律,都踏在谁的心上?
恍惚地想,恍惚想起初见。

过去得太久,重熙未必还记得,但是慕莘是记得的。
那时候她初上战场,探营归来,月冷如霜,忽然就瞧见旗杆下绑跪的小兵,不知犯了什么错,只着中衣,衣上血迹斑斑,被马蹄声惊动,抬起头,远远冲月下夜行人龇牙笑了一笑。
没心没肺的样子。
慕莘进营回禀过主帅,随口提及,才知道这名小兵是逃回来的俘虏,按律当斩,因众人求情才保得一命,但是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,日鞭三百,绑跪于战旗之下,已经两天两夜。
“两天两夜还不够么?”慕莘皱眉。
按律自然不够,但是当时主帅是慕莘的叔父,最是疼她,因这一句,收了剩下的惩罚。
过得年余,慕莘累功得进,主领一军。到底年少气盛,受不得激,打益城时轻身冒进,后继无粮,险些被包了饺子,幸而叔父得到消息,火速派人来接应,当时开城门,一个照面,看见盔甲下的那张脸,眉目宛然,脱口道:“怎么是你?”
楚先锋微怔,随即龇牙一笑:“怎么就不是我?”
怎么是他?
怎么就不是他?

二 与子同袍
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,不知道为什么,忽然就想起来。
许是月色太好。
这些年他们并肩打了很多仗,攻城掠地,所向披靡,连蛮人的可汗也都有所耳闻,誉以“龙锋双将”,美名传至京都,龙颜大悦,命画师赴边,录了两人的画像回京,连呼为“朕之长城。”
谁是谁的长城?
慕莘抬头看了一眼挺拔如松的背影,皎皎月华,让她想起两张流落京师的画像,心里猛地一沉。重熙不觉,仍同她说席间趣事,张耳如何被众将灌醉,李华怎样狡计脱身,最要不得的是曲南陵,设计贪了一桌子银器。他原本就口才甚好,这一晚更是滔滔不绝,连插嘴的空隙都没给她留下。
啰嗦得有点不同寻常。
也好,慕莘默默地想,拖得一时是一时。
十里长街走到尽,一抬头看见角楼。洛城是边境上最后一座城池,再往北就是漠漠草原,莽莽戈壁,塞外各族逐水而居,再没什么像样的建筑了,所以登楼看去,风吹草低,视野空旷至极。

值夜的士兵向他们行礼。
黑色劲弩在月光下泛着泠冽的光,慕莘伸手摸到弩台,要试一试弓力,忽又犹豫,比划了半天,又放下了。
她的剑术冠绝三军,箭术却一直为人所诟病。
重熙却是高手,当即笑道:“又不是弓,八百步的弩,有什么拉不开的……”边说竖起弩弓,双手同时发力,将弦钩至弩牙之上。
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太近,夜忽然就静下去,他凝神操作巨弩,她凝神看他,月光太喧嚣,而眉目温柔得像春水,慕莘听见自己的声音,低如蚊呐,她说:“我要走了。”——这一仗打完,洛城收入囊中,北蛮估计会上求和表,而她就要调回京师了,密函是下午到的,知道的人并不多。
弓弦险险一跳,银质的月光随之一荡: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?”
一朵乌云飘过来,月亮给它镶上银边。
漫不经心松了手,长箭离弦,远远听见惨叫声,不知道是那个窥城的倒霉鬼,重熙探身看了半晌,回头道:“兵部的命令,让我送你回京。”
“送我回京?”慕莘用古怪的声调重复,忽然放声大笑:以她龙锋双将之名,自边疆回京,竟还要人一路护送么?

真当她是寻常弱女子么!
她慕家世代簪缨,至这一代,父亲与叔父膝下无子,将她充作男儿养,自小在沙场摸爬滚打,血与火中,是凭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功名。
功名又有什么用?
皇家一纸聘书,三月之后,她就是这个王朝的太子妃,或为收她慕家之兵,也是皇家恩典,谁问过她慕莘愿意不愿意?
慕莘笑得弯身去,指甲掐入掌心,丝丝血腥,丝丝痛意,她忽地抽出重熙腰间佩剑,转身直奔下楼,冲进城南的修罗场乱砍乱杀,她原本就剑术精绝,心绪激荡之中虽然全无章法,剑下却是一个活口也无。
一场厮杀足足耗去大半个时辰,一直杀到城墙之下,慕莘仰头看见风中猎猎作响的帅旗,旗上斗大一个“慕”字,鲜红如火焰簇成的玫瑰,忽然双腿一软,支剑跪倒,哭声却还哽在喉中,不能发出来,只切切地想:从此,再不必背负慕氏不败之名。
风越吹越冷,青丝越吹越乱,不知道僵持了多久,身后人道: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慕莘勉力站起,还剑入鞘,面上再没有别的表情,只淡然应道:“好。”
就这样回去了,长夜静默,连饶舌的重熙都再说不出一个字。
她想听的话,他始终不肯说。
只是,说了又如何?

三 穷山恶水
半夜里忽然下雨,潇潇,在窗边听了一会儿,没留心就到天明。
辰时出门,门外停着马车,不知道等了多久,重熙在车夫的位置上,青衣小帽,竟也像模像样,等慕莘上车,帘子落下,一扬鞭,骏马长嘶,洛城就远远落到了身后。
回头要再看一眼,又想,有什么可看的呢?
车行辘辘。楚重熙是成了心要哄她欢喜,一路插科打诨,使出浑身解数,饮食起居都照顾得周全,慕莘有时候希望这条路永远都走不完,又嗤笑自己荒唐——她不是深闺女子,北疆到帝都要走多少天,难道她不知道么?
掐指算去,只余三五日。
宫深如海,以后,怕是再不能相见了吧。时闻空中悲啼,抬头但见天清如水,孤雁盘旋,心中郁郁,终究半字不能出口。
重熙却回头来,问:“在这里歇一晚?”
慕莘扬一扬眉,重熙笑道: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——总值得慕帅看一眼。”
慕莘一怔,脱口道:“到江州了?”
重熙颔首称是。

楚重熙是江州人,自幼父母双亡,身无长物,一穷二白投军,起初只为一饭之需,至于后来百战成功,青云直上,那是后来的事了,倒不负了“刁民”两个字……这些,慕莘自然是知道的,当下心生好奇,微微一笑道:“好。”
重熙鞭下生风,骏马拐了个弯。
抵达时候已经暮云四起。
几棵老树,半间草屋,久未修葺,摇摇欲坠,屋中干净得如同才洗劫过的城池,偏还积了厚厚的尘,饶是慕莘见多识广,也免不了张口结舌:“这是——”
“寒舍。”重熙一贯的落落大方。
慕莘看看草屋,又看重熙,她如今换了女装,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,好在重熙轻车熟路,迅速从破败的草堆底下拖出坐具与炊具,到月亮出来时候,竟也像模像样上了四菜一汤,两壶酒,相对而坐。
“离家这么多年,”慕莘环视屋中,许久方才挤出一句:“没回来过?”
“回来做什么,又没人惦记。”重熙耸耸肩,笑。

当初离家的少年才多大,才多高,是怎样千山万水走到边关,有没有发过誓有朝一日衣锦还乡,慕莘努力想要拼凑出他当时模样,当时背影,当时两手空空远走天涯的志气……但是终于拼不出来,便只叹一口气,灌一口酒,月亮照亮她的面容,她照亮了谁的眼睛?
都碎在酒杯里。
喝了很多酒,怎么喝都醉不了,又或者,一开始就已经深醉。
说了很多话,每一句都听不分明,也许是在问他,肯不肯带她走,离开军营,离开北疆,也离开帝都,男耕女织,一世的平和喜乐。
重熙笑吟吟举了酒杯,笑吟吟问:“阿慕你确定你会织?”那或是另外一个问题,但是慕莘笑了,如果他要的不是她,就算她无所不能,又有什么用?
但是醉酒的人不会察言观色,不会停风知雨,只固执地追问,一再追问:“你肯不肯、肯不肯?”
恍惚有人问她:“即便我肯,你就舍得吗?”
有什么舍不得。

她也许回答了他,也许没有,也许掉了眼泪,又或者没有,都记不分明了,以后,很多年以后,很多很多年以后,慕莘想起那个混乱的晚上,都还是混沌。
七窍开而混沌死,也许她当初,就不该追问得这么清楚。
--
醒来在慕府,头痛欲裂,母亲殷殷喂她醒酒汤,慕莘努力把碎成一片一片的脑袋捡起来,理清楚来龙去脉,问:“送我回来的人呢?”
“走了。”母亲心疼地看着她:“便是喜事,也不当喝这么多。”
母亲以为是喜事——她与父亲征战这么多年,母亲就在家里,心惊肉跳了这么多年,好不容易没缺胳膊没少腿平安归来,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,一世安稳,母亲自然以为是喜事,慕莘心中酸楚,也不反驳,只追问:“没留什么话吗?”
“没有,”母亲想一想,加了一句:“打发了不少,你放心,这些事,娘省得。”
慕莘苦笑一声,再无言语。

四 厄变
家中诸事不劳她操心。
九月归家,十月里贵客上门,父亲唤她前厅奉茶,茶烟袅袅中温雅清隽的男子,修长白皙一双手,含笑接茶,说:“多谢。”
声音亦温沉有礼。
未尝不是良人。
就此定下。采纳,问名,纳吉,纳徽,请期毕,时间定在三月三。日子恍惚过去,浩浩汤汤,又静水无声,有时想起重熙的面容,有时又想不起,就如同最后混乱的一夜,也许与她对饮的,根本就是她自己,也不一定。
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一夜。
眼看时间临近,便只在府中,跟母亲姨娘学穿针纳线,针尖扎进手指,并没有太多痛感,血染在嫁衣上,也不过是红得更深一层,不大看得出,但是母亲非逼着她重绣一幅,说是污了,做嫁衣不祥。
于是遵言换过。
多少年以后慕莘还记得那样一些时日,母亲坐在她身畔,教她如何下针,如何辨色,如何界线,闲时絮叨些家常小事:旧年的梅花雪泡茶最好,李家的表姐新生了孩子……早春的阳光从树叶里漏进来,将时光染成青翠的颜色。

皇帝的诏书就是在这样的时光里到达的,乌鸦鸦跪倒一地的人,大红袍子的宦官用尖细的嗓音传达上位者的意思,陈述一些事实,一些结果,关于太子的谋反事宜,最后轻飘飘抛出皇帝的判决:株连九族。
然后刀忽然就染了血,有人哭喊,有人挣扎,有人奔逃,有人倒下去,母亲用力推开她,说:“走!”雪亮刀尖从背后穿出来,慕莘下意识去扶,满手的血,滚烫……烫成她掌心里最后的纹路。
走!走!走!惶惶然,惶惶然就只记得这个“走”字,本能地杀出一条血路,又惶惶然地想:走到哪里去呢?她的家在这里,她的家人在这里,她的母亲在这里,那么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
于是再难走远。荒郊野庙,寄生一日一日。
不知道过去多少天,饥饿让她失去思考的能力,破的庙顶,日光与月光轮换,淡银色的星光洒在衣上,熠熠生辉,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有人进来,慕莘握紧手里的刀,没有动身,也许只是云游路过的僧人,或者乞儿。
都不要紧、不要紧、不要紧……她这样安慰自己。
但是脚步径直朝她过来,不慢也不快,不轻也不重,却坚定地,清晰地,一步一步,一步不停朝她过来,慕莘听见自己的心跳声,就仿佛过了一百万年那么久那么久,她五指一紧,刀光劈落——

“是我。”来人握住刀锋,那个声音像是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,那么远那么远,远到犹如在梦中,慕莘努力抬起眼,想要看清楚他的面容,却是怎么也看不清楚,隔得太远,隔了山,隔了水,隔了生与死,这个人应该在北疆,继续打他的仗,立他的功,升他的官,在打了胜仗的晚上输得精光。
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……会在这里?
慕莘呆呆看住眼前的人,他握住她的刀对她微笑,一滴血沿着刀身淌下来,流到她手上,虎口的温热让她想起洛城——不是梦。
当然不是梦,梦里怎么会有这样真切的眉目……梦里只有哭喊,挣扎,鲜血,母亲绝望的目光,还有最后,手心里滚烫如刀割的掌纹,慕莘怔怔地想,怔怔地,笑了一下。
啷当落地的刀。
“对不起……”他上前抱紧她,用力地,像是要将她整个人都嵌入他的身体里,嵌入他骨肉之间,再不分离,他将头埋在她糟糟的乱发里,闷声道:“我来迟了。”
迟,是,太迟,她生硬地回应他,她木然地想:可便纵是他来得早些,再早些,又能改变什么呢?
“跟我回去。”长久的沉默之后,重熙低声说:“你放心。”

他并没有说让她放心什么,但是她就这样信了他,由着他带她回去梳洗,由着他帮她换过衣裳,由着他亲手送她进监牢,隔着栅栏,他对她说:“……信我,总有一天,我会接你出去。”慕莘忽然不可抑止地笑了出来:信?信他?她还能再信他么?她还能相信什么?这样一个无常的世界,她还能相信什么、相信谁?如她此刻手中有剑,她或会如洛城破城那晚一样,将这个古怪无常的世界劈得粉碎!
然而她没有,没有刀,没有剑,连针头线脑都没有,沉重的镣铐,密密匝匝,从脖子一直锁到脚后跟,说是楚将军的交代,她功夫高,要严防死守。
严防死守,是怕她逃吗?
慕莘叹一口气,不不不,她不打算再逃,她已经听说了,慕府上下三百四十二口,除她之外,无一生还。
心如死灰,过去多少天,从来没有计算过,只盼着那一日,有人送来美酒,佐以佳肴,然后选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,送到午门去,就在她慕家三百四十一口倒下的地方,与这个世界一刀两断。
相信她的鲜血喷出来,也不会比别人更艳。
慕莘仰起头,微弱的光从天窗里照进来,苍白一缕,没有颜色。

五 南方
慕莘心心念念等着断头的日子,一直没有到来,连狱卒都没有过分为难她,过完春,接着是夏,到秋天的叶子落下来,忽然牢门开了,她再一次看到重熙,全身铠甲,英气逼人地站在面前,就仿佛时光不曾流逝,还是她与他,并肩作战的岁月……他说:“阿慕,我来接你出去。”
那是他的诺言,他用了两年时间,转战南北,他用所有功名,换她的命。
关于龙锋双将的这段情缘,在大夏朝有许多传说,他们活着的时候很多,死去之后仍有很多,如果不是更多的话,据说当时慕莘伏在重熙怀中恸哭,重熙殷殷看住她,殷殷地说:“做我的妻。”据说他用了一个陈述句,并没有给他深爱的女子留下反对的余地,当然无论是谁,对此情,当此景,亦找不到反对的理由。
其实……并没有。
传说只是传说。
现实中少有这样的戏剧化,事实让,重熙只是让她跟他走,她就跟他走了,没有问他去哪里,做什么,就如同当初他让她信他,她就信了他,一句多话没有,一滴泪也没有,血与火中淬炼出来的人,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眼泪,而血与火中淬炼出来的情缘,有些话,在她与他之间,原本就不必说也不必问。

她也没做他的妻,因为新任的皇帝不允许。她是一个罪臣,或者罪臣的女儿——无论这罪过与她有多大关系,毋庸置疑,她是有罪的,而重熙还有大好前途,无论在世人还是皇帝眼中,他救她出牢门,已经仁至义尽,他应该娶一个能与之匹配的妻子,作为他平步青云的垫脚石,或者由皇帝指婚,以平衡朝中错综复杂的关系。
总之她都没有机会。
所有他们应该拥有的,所有他们能拥有的,原只是夕阳里一段最后的并肩同行,哪怕影子被拉长,重叠,恍如当年月下。但是如止于此,那不过一段俗世悲欢,如何当得起绝世传奇,被后世长长久久地流唱、长长久久地艳羡?
但是如果仅止于此,对他与她,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
慕莘以为重熙会带她回北疆,那是她熟悉的地方,有她熟悉的天气,熟悉的城池,熟悉的风沙与月光,但是重熙说:“不,我们去南方。”
慕莘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了南方,第一次看到这么绿的山,到秋天还郁郁葱葱的树,鲜红的果子从树上一串一串倒垂下来,仿佛仕女别致的耳坠;第一次看到这么宽的河,河水清清如镜,映出人影成双;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迤逦起伏的山丘,蜿蜒曲折,千姿百态,连绵不绝,如画。

南行月余,抵达卫所。
没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漠漠,更没有黄沙莽莽,甚至没多少地方可供跑马,当然如今的慕莘也不需要再跑马,她已经不是将军,连兵都不是,她窝在将军府里,一日一日盯着蜿蜒的绿萝发呆,只有重熙归来才有片刻的欢喜。
这片刻的欢喜,与手心里滚烫的掌纹,支撑她活下去,日复一日。
但是重熙得闲就拉她出门。
有时是爬山,慕莘功夫搁下已久,不过几步路,走得气喘吁吁,重熙耐心地跟在她身后,亦步亦趋,低声说笑,有时说旧时光,那些早已死去的名字,那些仍镇守北疆的同袍,那些在黄沙中寻找绿洲的往事,以及他当初在草地里伏击狐狸给她做狐裘的笑话;有时说他才到南方时候的惊异,有无数不认识的花,无数不认识的树,许许多多看似美丽实则危险的飞禽走兽,他说他在深林里抓了很多只雉鸟和野鸭子,用它们的头羽给她做了件大氅,到冬天的时候穿着它走在雪地里,会让人疑心有凤来仪。
慕莘爬得累了,他就背她继续,一直到山顶,看旭日东升,金光万道,他说:“阿慕,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时光,可以从头来过。”

这时候慕莘多半已经睡熟,在梦里,已然紧锁的眉,重熙将她放在树下,戴上一路编好的花环,轻吻她沉睡的眼睛。
有时是划船,乌篷船小小,在水上晃荡,慕莘初来,站立不稳,重熙就搂住她,看长的桨划出长长的碧痕,艄公扯开嗓子唱歌,粗犷的声音,古怪的腔调,长长短短,短短长长,惊起水鸟无数;
后来渐渐习惯了,就不带艄公,重熙亲自操桨,如果是清晨,乳白的雾气在水面弥漫,咫尺之近的人,咫尺之近的眼睛,都朦胧起来,仿佛一眨眼就会失去,慕莘紧挨着重熙,头靠在他肩上,重熙于是也笑着唱歌给她听,歌里说,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;如果是深夜,漫天星斗都沉在水中,伸手就可以掬起,而莲叶渐渐田田,菡萏出水,愈上愈妍,重熙下水给她摘莲花莲藕,脆生生的菱角,满口甘甜。
如果这时候面前有面镜子,慕莘会发现自己眉梢眼角的笑意。
重熙却皱眉,无限苦恼的样子:“唷,养胖了诶,背不动了呢,以后爬山可怎么办……”
慕莘恼羞成怒,兜头兜脸砸过去一把莲子。
也并不是不欢喜的。

六 如果
如果。
慕莘不是没有想过,如果自己甘心于此,甘心忘掉三百四十一条人命的鲜血,甘心不去查找当初灭门的冤头债主;如果重熙能够遮住她的眼睛,捂住她的耳朵,捆住她的手脚,让她看不见听不到动不了,像寻常妇人一样,只能在庭院里,等着四角的天空,从苍白到湛蓝,湛蓝到深黑;又或者,如果他阻止她,让她在将来与过去之间二选一,或者执着于复仇,或者与他共度此生……如果。
她无数次想过这些如果,在后来,在许多个不眠之夜,辗转,无数次想,如果她此生,从开始到最后,都有这样的欢喜,能与重熙厮守日日夜夜,能泛舟水上,逍遥天地间,朝朝暮暮。
如果。
或有人这样的幸运,奈何不是她慕莘。
她终究是……修罗场中爬出的厉鬼,便纵然有人珍爱她,有人守护她,她还是会长出尖的牙,利的爪,将仇人的心肝从腔子里挖出来,祭之于亲人灵前。
她相信她的爪子伸出去的时候,重熙是有所察觉的,他是那样敏锐的一个人,但是他照常给她画眉,画得轻如远山,翠如新柳,然后在出门临别时候笑话她,抬头陌上杨柳色,有无悔教夫婿觅封侯。
慕莘扬眉应他: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!”

重熙的笑容僵住,他轻轻吻她的眼睛,他说:“阿慕,我只想你欢喜。”
慕莘说: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不知道!”重熙低声说:“当初,当初我们还在北疆的时候,我第一次看到你,你探营归来,蒙着面,我看到你的眼睛,明亮得就好像月亮落在水里的影子。后来我们并肩作战,我救过你的命,你也在我重伤到所有人放弃的时候还守着我,那些时候我从来没有忘记过,后来你说要走,后来我送你回京,在江州的那个晚上,你问我有没有想过衣锦还乡,我没有,阿慕,我是个胸无大志的人,我从来没有痴心妄想过有朝一日能得你朝夕相伴,这样的日子,别说有一年两年,就算只有一天,一个时辰,一刻钟,甚至是一个刹那,我都会觉得此生圆满,再无遗憾,所以阿慕,无论你做什么,无论你要去哪里,无论你在不在我身边,我都只想你欢喜,你……明白么?”
慕莘说我明白。
重熙微笑,转身要走,却听的身后人轻轻地问:“你既然还记得江州时候我问你的话,那么,你当时为什么不带我走?”
如果当时他应她,如果当时他带她走……重熙没有回头,背影里黯然与萧索,萧索如这个秋末的风,他说:“阿慕你说傻话了,即便当时我肯,你也是不肯的。”——即便她肯,他又如何舍得她去过那些漂泊天涯,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那或是真的,如果当时她不归京,就是明目张胆抗旨,那又置她父母家人于何地?所以这样一个结果,原是他与她命定的劫数。慕莘于是点点头,将声音压得更低一些,她说:“重熙,我或要回京一趟。”

重熙微不可觉地叹了口气,并不问她回京做什么,只道:“……还回来么?”
“如果你不怕……”
“只要你肯回来,”重熙重复:“只要你肯回来,无论什么时候,我都在。”
那是他的承诺,慕莘闭上眼睛,这样,就不会有眼泪流下来,你知道么,有时候眼泪和鲜血一样,会在灵魂上烙下透明的印记,无论辗转轮回,还是三生石上,孟婆汤里,相爱的人总能看到。
——这时候她已经从盘根错节的关系中理出头绪,边边角角的人物,该杀的杀了,该埋的也埋了,所有明线暗线最终都指向金銮宝座,要细想并不奇怪,不过是双龙夺嫡,池鱼尚且遭殃,而况慕家铁杆太子党。
行刺九重宫阙,多半有去无回,就算侥幸回来,只怕从此也要亡命天涯。
但是重熙说他会在,无论什么时候回来,他都在……但其实她有时会希望他不在的,慕莘从背后抱住他的腰,把头靠在他背上,低声说:“等我。”
等我回来……杀你。

尾声:绝世
慕莘回来,在来年的春,南方的雨,淅淅沥沥下了整月,这一日偏停了。就如同第一次见到重熙时候一样,蒙面,夜行,随风潜入,在他的床前,看他沉睡的容颜,恍惚地想,竟然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么多年……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,一丝一线织成岁月的经纬,无论沿着哪一丝哪一线看过去,他都是她避不开的劫。
是的他爱她,不会有人比他更爱她。
所以她还是回来了,在深夜里,在月光下,等长夜慢慢到尽头,等第一缕霞光在苍白的晨曦里浮起,等他看到她,她说:“我要回北疆,重熙,你跟我去么?”
重熙微笑:“去。”
那或是他们最后一次同行,据说狐狸死去的时候,头必朝向出生的山丘,所以他们死的时候,一定要回北疆,回到当初笑过哭过,相遇过相爱过也相别过的北疆,慕莘对重熙说:“当初你说要做一件狐裘给我,当初没有做成,如今……你可还愿意?”
重熙说:“我自然是愿意的。”

他于是上马出城,这时候士兵都被遣开,慕莘独上角楼,竖起弩弓,双手同时发力,将弦钩至弩牙之上——多年前,她离开的北疆的那个晚上,重熙曾给她演示过,慕莘转动弩弓,瞄准,松手。
长箭离弦而去,对准她此生最爱的人。
他原本不必送她回京,原本不该这么快就出现在京郊的荒庙里,原本不该拒绝皇帝的赐婚,这样,她最多不过是疑心,而永远不会去正视,不会,永远永远都不会,因为那是他的罪,又何尝不是她的孽。
她不舍,不忍,亦……不敢。
不得证实,便可以假装不知道,假装不知道他是皇帝的人,不知道如果不是她的亲事,所谓太子的叛乱不会提前发生,虽然那或是她慕家在劫难逃,但是他的手上,终究染了慕家的血。
假装不知道他为她颠覆的天下。
他是知道的。从她开始动手查案他就知道会有这样一个结果。
他没有阻止过她,或因他知道,此事不了,她终身都再难得欢喜。

他知道,所以纵容。
他不得不拒绝皇帝的指婚,不得不被她觉察的黑手,他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离开,所以他在她离开之前将所有想说的话,一次说给她听,因他知道以后再无机会,当她归来,如果她还能活着归来,便是他与她共赴黄泉。
如果她不能……他亦不会让她独自过奈何桥。
所以他从不问她为什么要回北疆,不问她为什么忽然要狐裘,他说过他只想她欢喜,所以一直到最后,最后的最后,长箭穿心而过,他尤自回头来,微笑,微笑着看他深爱的女子反手,将匕首插入胸膛。
生不同时死同时。
那时候天色将暮,而红霞满天。
【完】
-
2019-03-24
-
2019-02-28
-
2019-02-28
-
2019-02-28
-
2019-02-28
-
2019-02-22
-
2019-02-22
-
2019-02-20
-
2019-02-20
-
2019-02-20
-
2019-02-20
-
2019-02-20
-
2019-02-14
-
2019-02-14
-
2019-02-12
-
2019-02-12
-
2019-02-12
-
2019-02-12
-
2019-02-12
-
2019-02-12
- 今日必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